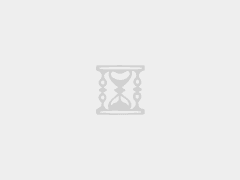江南是一个很广泛的地理上的概念,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都可以看做江南,而且历朝历代,江南的范围也有所改变。
江南是相对于江北而言的,在艺术上,一条长江把中国的艺术风格大致分成两个流派,如果细致精美,我们便称之为江南风格,然后粗犷豪放,我们便称为江北风格。
要了解为什么江南多出文人,要从古代的地理经济政治上来讲文化。
地理上江北多以畜牧为生,江南多以种植为生,江北气候苦寒,冷的时候只能号两嗓子给自己鼓鼓劲,江南气候温暖,更适合缩在家里听小曲。北方人还在愁食物的时候,南方人在读书。北方人居住比较分散,南方人居住比较密集,因为南方更容易养活更多的人口。
经济上,北方以畜力驮运作为运输方式,而南方有密密麻麻的水网,可以用船运载,北方物产不多,所以经济不发达,南方物产丰富,民众经济交流频繁,交流频繁带动文化的传播。
政治上,北面一直是比较动荡的地区,远不如南方安定。宋朝南迁就是如此,南方有比北方更稳定的生活。
所以在北方文士被战争,被饥饿,被寒冷愁白了头的时候,南方的水稻一年两熟,南方物产丰富,交通便捷,交流频繁,南方生活安定,民众有固定的住所,可以将书籍一代一代传下去。
所以在文征明那个时代,进士几乎都是南方人,而以精致秀美闻名的书法家,也大多是江南人,比如吴兴某某某。
拓展资料: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经济富庶且北方战乱不断,社会极不稳定,人口也开始大量向南迁移。
古时,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河流阻碍了人们的出行,所以最先北方国家强盛,但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水运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且南方气候温和降雨多,农作物宜生长,渐渐南方活跃起来。
江南山清水秀,云碧烟寒,气候宜人,既没有北方的寒冷,也没有偏南的酷暑,气候、植被兼有南北的优点,所以中国的山水名胜与古典园林,除去皇家园林,多位于江南,自古以来多集于扬州、苏州、杭州。江南的风物人情,火红江花、池塘水满、花木葱茏、如蓝江水、山寺桂子、郡亭潮头、春竹吴酒、芙蓉娇娃,都是催人的风景,也是醉人的新梦。是文人的企盼,更是文人的眷恋。江南的四时风光、梅雨风絮截然不同,风土人情,殿堂馆阁,别样韵味。
中国北方的战乱,也一度让北方名士、大户望族纷纷南迁,为江南地区带来了新的血液。
由于北方环境恶劣,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教育,特别是在北方圣人孔子的殷殷教诲下,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下子让江南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
由于南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远离蛮夷,像北魏孝文帝,都把都城迁往南方,为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经济是基础,经济发达自然人口多,生活好了,诗情画意,自然兴盛起来。
他们迷恋江南,不仅是景色好,更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
古代文人眷顾江南,也是因为江南蕴涵了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特别是古典文人无不都是徘徊于儒与道、出世与入世、此岸与彼岸之间的矛盾情结。古典文人的这种矛盾心理情结大致可归为三点:闻达经世,放浪形骸,归隐园田。三者并非互不关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中国古代的文人,特别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寒士,无不在三者之间辗转,非此即彼。绝大多数文人都不曾摆脱这种所谓的古典文人情结的束缚。
传统的文人也常常从江南的山水园林、田园牧歌中寻求一种自我慰藉的精神力量,于是,文人们也就有了另一种情结,那就是归隐园田。这些古代的文人们笔傲山林,归隐园田,这种逃避社会的行为在文人世界中很流行。于是,文人们还发明了各种隐逸的方法: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在内心极度的矛盾中自我排遣的一种人生策略。不管这些古代的文人们是哪种情结,但都没脱出江南的气质,只能是更加体现出他们骨子里的江南文化内涵和文人们皈依江南风情的山水情结。
古代文人普遍而根深蒂固的江南情结,千百年来已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行为意识深深植根于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内心深处。其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得意与失意文人都可以在江南寻得一种心灵的解脱,他们几乎都在江南这片美丽而人杰地灵的天地里将他们的人生艺术化、审美化,并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诗意化。如果从纯文学的观点出发,人生的艺术化需要以内在的诗意拥抱生活,发现生活中瞬间的诗情词意,并逐渐培养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情致。而那种感性的自然陶冶,灵魂与智慧的自在升华,意志与坚忍的融会贯通,当然需要江南天然美景的溶汇,才能最大限度激发文人们的文思与情思,才能创作出流芳千古的不朽诗歌词赋。
江南正是古代文人们人生艺术化、思想审美化、日常生活诗意化的最好自然载体,江南的人文地理、风物气候都洋溢着自由浪漫的诗情画意,是涵养古代文人身心平衡的天然方剂良药。任何一个古代文人,只要身处江南,就会情系江南,就会梦忆江南。从白居易到朱自清,他们不约而同地殊途同归,都在江南意象中获得寄身养命的家园,真可谓“千古文人,江南一梦”。
 小人物K
小人物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