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伊斯坦布尔》第29页上一张公共汽车在雨中行驶的照片,我来到了另一栋衰老的屋子里,这是二十多年前我生活过的地方。或许是此刻雨水顺着玻璃窗淌下的痕迹,还有窗子外面冒雨行驶的公共汽车,让我想起了自己曾在某个早已忘记的童年早晨,静静看着雨水从屋檐滴下。我,面对面的两间平房,几棵高大的杨树,都在雨中安静地存在。起初,只有叶子发出的簌簌声,接着,便有了雨滴在水缸里的水的声音。
当一个人去想过去的事情,就好像在看一部慢放的电影。时间愈久远,胶片就转得愈慢。一片记忆中的叶片用了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落到下水道的盖子上。而那个比我大点的小伙伴将手电筒对准某颗星照过去,他在照手电的同时还对我说,“这些光总有一天会被外星人看见的”。
下次遇见这位朋友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这些光没有照到另一个世界,而是印在了这个世界的未来。但可惜,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他了。他当年幻想外星生灵时所站立的地方,已经沉入地下,成为一栋楼房的地基。在那座山峰般的大楼里,有数百人在洞穴般的房间里每天乏味地生活。
哪一种情况更有趣呢?是手电的光经过几亿光年的旅行,照在一个正在外星黑夜偷窃的小偷身上,一个中年男子突然想起某个童年时光?我觉得后者才是真正的生活,前者更像是出自好莱坞导演之手。当好莱坞统治一切的时候,电影就已经失去了想象力,一种失去想象力的想象力。
我从小并不喜欢电影,因为我老是不知道电影在讲什么。但我记得这个城市每一座电影院的样子:从一进门的门厅里摆放的游戏机,到出口旁边的厕所里的满是锈迹的水管。有的电影院的厕所就在门厅旁边,一进电影院就会被那种难闻的味道包裹。每一次看电影,我都随着一群欢天喜地的同学,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灯光熄灭,一阵激昂的音乐声中,《新闻播报》开始了。当时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影片中的那些欢乐深印在记忆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霹雳贝贝》,我看这部电影的地方叫做皖江电影院。电影中有个被外星人赋予神力的男孩,他带着一群孩子在停电的游乐场肆意玩闹。玩闹之后又贪婪地吃下一块块香甜的糕点。而在前往电影院的路上,我曾遇见了两个街头卖艺的男子。其中一个用只剩半段的手指钻透了一块红砖,接着举起磨破的指头向围观的人推销自制的药丸。“我不是卖大力丸的!”他大声说,最后一个字斩钉截铁。而另一个比他更年轻的男子,用更大的嗓门重复“不是卖大力丸的——”,像回音一样。我入神地看着他们用粗糙宽大的手掌,重重地拍在胸脯上。我还在他们要求大家检验红砖的真伪时,混在人群中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是真的!”我的内心一片欢乐,这种欢乐是来自对神秘事物的见证——尽管我当时也猜想:药应该是假的。
这次欢乐,以及之前和之后无数次的欢乐,被留在某个时空中。我常常花很长时间去寻找它们:在记忆中翻箱倒柜,最后,也许在一个湖畔的芦苇——在夕阳的金光中融化的芦苇——的白芒中发现它们的踪迹。有时候,我都会嘲笑自己,简直就是《超越时间线》中滞留于过去时光的罪犯,虽然制造出一起又一起足以改变未来的事件,但又无法前往未来去验证结果。因此,他们必须常常自我鼓励,对自己说:“我可以改变未来,而且未来已经因我而改变”,否则,他们会连犯罪都提不起兴趣。他们还需要时时构想因他们而改变的未来,这就像是给自己拍摄一部电影。
而电影里的那个漂亮女警也同样要时时想象,未来正在她的维护之下在正常的轨道安稳地滑行。警察和罪犯的对峙,好像是两个电影大师的交锋。
电影都是迷宫。每一个人物,都是可能的路标。看电影的人,在观看中,被时间之流不停地被推向不同的入口。暗与光,生与死,柳暗和花明,自性与他性,纠葛与弃置,观众始终在两极间摇摆,有时像做过山车一样惊慌失措,失声大叫。但有时,我们又像走进一间小屋,透过淋着雨水的窗户,打量匆匆走过的人和车。每滴雨水都在玻璃上留下一道印记,使得观看者的视线在透过玻璃时产生微小的变形。是的,一定会变形——哪怕是所谓的纪实作品,也在暗地里新建着观看者的世界。电影,假装自己是记录者,其实却扮演了导师的角色,要用自己的观看来代替我们的眼睛。
没有哪一种表达不带有征服的欲望。反过来,一个沉默的人,一个常常对自己的说话的人,也许是在向内征服自己。他会经常带着自己驶向不同的远方,比醉驾还要疯狂。“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在哈姆雷特问自己之前,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可一旦他开口了,他便领着自己走进近疯狂仅一步之遥。
对我来说,回忆,就是一场小津安二郎式的电影。秋风袭来,而我在听《黄色潜水艇》。酒馆里的海军中校要了两瓶淡酒。世界如一滴屋檐下的雨那样安静。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这样说,“我喜欢由秋入冬的傍晚时分,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看着旧公寓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这些话比傍晚的街道上那条孤单的狗还要忧伤。
十岁的我,曾经像童年的帕慕克一样,藏在玻璃窗后,打量着一个庞大的世界正在走向黄昏的身影。下了班的人们穿着灰色的衣服,钻进黑白电视中的武侠片。“这是黑白城市里的穿着打扮,他们仿佛在说:这是为一个衰落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哀悼的方式。”帕慕克这样说。而这也是对二十年后的我说的,只有当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来回忆往事时,我才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城市从繁华到暗淡的忧伤。我想起一位同乡作家对我说,他毕生都在为写一部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作品在做准备。他心中的伊斯坦布尔就是安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仿佛听见帕慕克在说,动手吧,快些“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我们的昔日传奇梦。”
是的,别耽误时间了。雨水从屋檐滴下。滴到檐下的水缸里。一切都在冬天发生。而现在已经是秋季
 小人物K
小人物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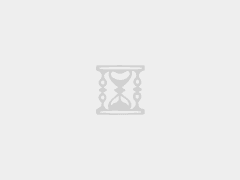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