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第一次读到《苔花》时,便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野草》,还有他写给青年的《导师》: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我原先不觉得这句好,但看了《苔花》后,有点发现了其中的好来。
《苔花》说的是人的愿望——“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但是,是谁的愿望呢,是卑微者的愿望。什么样的愿望呢?是卑微的人渴望能像富贵者有一样的生活权利的愿望。愿望是对的,错的是袁枚。他制定了牡丹和苔花的二分法,并且理所当然地将牡丹作为了苔花的榜样。因为袁枚不是卑微者,他是“牡丹”,是享乐者。他高高在上地对“苔花”说,你们要坚强、要努力,却不说,怎么才能开放。可能,他也不会关心怎样才能开放。袁枚只是写了一句聪明话,当时人说“巧语”,现在话说是“抖机灵。”
他没说的,他根本没有体会到的,鲁迅说了——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怎么才能开放,一要拼命,二要不认命,三要靠自己。鲁迅不会把人分成牡丹、苔花,在他眼里,只有老人和青年。而且这也不是指年龄,而是生命力的旺盛和衰退之别,是思想的进步和腐朽之别。
他讴歌青年,讴歌在黑暗中点亮火炬的人。“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他尽管知道力量微弱,但也要尽力的发光。如果他真的写了一首苔花,也只会写苔花拼了命地生长,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与牡丹又有什么关系!
不要说苔花,在鲁迅看来,哪怕是野草都要展现出生命的力量。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如果鲁迅自欺,他大概会说只要努力,连野草会长满世界。但他不会,他知道野草再怎么生长,都会遭到践踏、删刈,也会死亡和腐朽。但他没有为此而悲哀或是绝望。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展现生命本身,在于爱与尊严,在于他人的幸福,在于牺牲和奉献,在反抗和斗争,在探索与进取。
而不是“学牡丹开。”
而且,学也是学不了的。我觉得《苔花》忽然红遍,一方面是因为卑微者的愿望,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社会充满了对“阶层固化”的担忧,大家害怕“苔花”再怎么开,也不会和“牡丹”一样。
是的。苔花永远不可能成为牡丹,除非我们既不自认为是苔花,也不要把谁当做牡丹。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是牡丹,也不要被他吓着了。
 小人物K
小人物K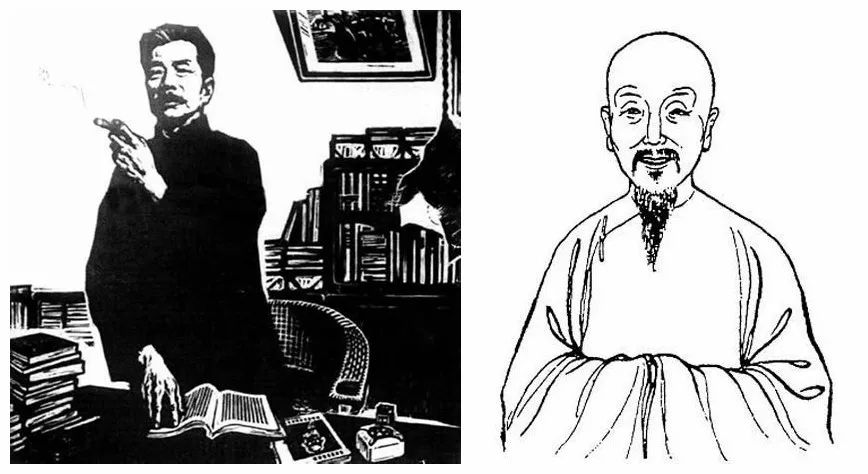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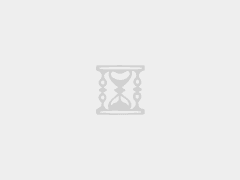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