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遇见,一个人,是歌兰。
我低着头,带着孩子走。突然看见迎面来的人对我笑,帽子,围巾,包裹得严实,只露出一张脸。仔细看,是歌兰。
“你怎么到这来了?”
“过来看看我妈,我不住这里。”她说,“我现在基本在某地方。”
“住某地?”
“是的。”她点点头。
我有很多年没见过她了。2000年左右,我和一些文学上的朋友、老师去拜访过她好几次,她不太说话,但对诗歌认真。我把写的东西请她指点——她那时已经参加过“青春诗会”,很有点名气了,却一点也不嫌弃地读完了每一首,并且在稿子上写上自己的意见——都是些鼓励的话,但当面交流时,她就直接得多了,指出了我的很多问题。
歌兰是怀宁人,最开始的诗歌也有点海子那种乡村意象。但有一次,她和我们谈起本地另一位诗人颇具荒诞色彩的作品:
“车是火车,雨是酸雨
你遇见的我,是第二次的我。”
她真诚地说:“写得真好啊。这么简单这么好。”
我们当时都很喜欢那位诗人的作品,但真的没想到她也会喜欢。只能说,诗歌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个人风格的不同并不重要。
后来,我的工作渐渐忙起来了,没有时间写东西,也没有再去拜访她。有一次在路上遇见她,她说你有首诗写的不错。我觉得欣喜,也诧异,因为那首诗应该是很久之前发表的。她说,前几天寄东西给一个朋友,拿了一张旧报纸包着。朋友也是写诗的,接到东西后顺便看了一眼报纸,觉得上面的诗还不错,便打电话告诉她了。
2014年的一天,她送了我一本刚出的诗集《稀薄的门》。我有时翻翻,有些看得懂,有些也不懂。
这几天,因为遇见她,于是又拿出来看。还是似懂非懂。
她写“幸福吃掉了你的骨头”,写“数着星星从你眼前走过/这也许是最好的一年”,写“最美的植物人”
还有《即兴》:
就坐在这样的石头上
江水就在脚边
轻轻地打着拍子
又回到了从前
粗枝,大叶
没有智慧
像个纯粹的食肉动物
我虽然不懂,但还是很喜欢这些诗。诗不需要懂,而是一种气味,有时是糖果,有时是血,有时是薄雾里的森林,有时是我在建设路和人民路口闻到的从水师营飘过来的鱼腥味。
在存在的意义上,懂是无意义的。这个世界不是仅仅靠理性就能把握的——更不要说没有理性的头脑了——人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只有以全部的生命激情,通过感性的参与,才能生成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一个诗意的世界。
 小人物K
小人物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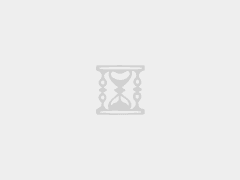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