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什么呢?你那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伤逝》
我知道一个女性在这世上是很难的,一个有追求的女性是更难的,一个有追求并且付诸行动的女性是尤其难的,但带着对这世间人性的一丝丝美好期待,我是不愿承认子君死了的。毕竟谁也没有说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宁愿怀着幼稚的美好的期待:也许子君只是被远远地送走了,她也许是被送到了外地去了,甚至她也许是出家了从此青灯古佛静谧安宁了。
子君是个美好的女性,她美丽温婉但勇敢坚定,她说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样子一定是极璀璨热烈也极美的,我仿佛能看到希望的火焰在她眼睛里烧。可这火焰是什么时候变小的呢?是涓生说“我不吃”的时候吗?还是在每天“川流不息”的做饭中消磨掉了?还是将阿随推到土坑里的时候呢?不过,我知道她的火焰是何时熄灭的,是在“我已经不爱你了”话音落下时,是在“说她去了”时,是在留下几十枚铜元时。是的,躯壳腐朽之前,心是凋零了的。
王尔德在《当模特的百万富翁》里说:要是不够有钱的话,魅力也没有什么用处。浪漫是富人的专利,却不是无业游民的行为。这话不仅在伦敦适用。涓生的爱就是被无业给消磨了,然后虚伪了,然后怨恨了。我不想只单单批评涓生为所谓“渣男”,这是时代的不幸与悲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谈论爱情与面包,不过那时的涓生要的不过是一份尊重与工作,我们谈的是房子车子和年薪,到最后大家也都是不敢说“结婚”的,而子君到了死也只得了个“朋友“。子君的家庭大抵是富庶的,她上学双手白嫩且不会做饭,只做了几天家务双手便粗糙起来,可见之前不是娇小姐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所以她的理想主义是单纯的而不是纯粹的,没见识过黑暗的投奔光明可以说一声粗鲁与莽撞,就像没见过阴暗便算不得有见识一样。
我想到了台湾省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也不免想到了印度的那个美丽黄昏,一个美丽的少女和她心爱的人在海边看美丽的日落,他们在这里私奔,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哪里又容得下他们。过了几天,也只剩下了男孩一个人说着“她被带回家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我再也看不到她了。”是的,世界从来不缺光明,所以只要壁垒存在世界也从来不缺阴暗。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印度社会是否需要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大革命,也不想批评在社会浪潮裹挟下人们的思想不够进步,这样的语句太过傲慢。进步与觉醒是无声无息毫无征兆的,就像长大,我们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哪个瞬间我们忽然就明白了一些道理理解了一些人看懂了一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我到底有没有长大,什么时候长大,之后还会不会继续长大,但我可以等,我已经接受了我是个晚熟的人了。
 小人物K
小人物K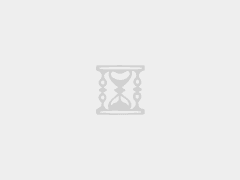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