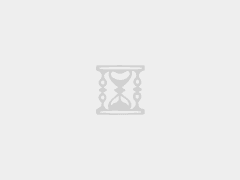今天讲几个小案例,不做价值判断。
案例一:某个地方要修路,道路要经过一所民房,房主不想搬迁,于是公民投票决定该不该搬迁。结果大多数人同意让房主搬迁,于是房主不得不被搬迁。这个案例是我在UIUC进修的时候老师讲的,他让我们思考,这样做对吗?我们说可以。他接着问:如果你们小区投票让你搬家呢?
案例二:天降暴雨,某地大坝有决堤的风险。如果泄洪会保住大坝,同时保住下游一个最重要的大城市,但是会淹没旁边一个小城市。我们该怎么决策?很显然,我们都知道要保护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价值更高。我如果说小城市难道不是城市吗?肯定会被耻笑。
案例三:大家看过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牺牲好多人为了救一个人,值得吗?
案例四:开车就会出现车祸,为了保护行人,是不是禁止开车?吸烟喝酒就会出现死亡,是不是禁止吸烟喝酒?
案例五: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第二年他就对犹太人大批地监禁和屠杀,然后发动世界大战。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犹太人的悲惨处境是民主制度造成的呢?如果换一个制度,或者换一个规范,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就可以逃过一劫?恐怕不能这么说。
案例六:在一场战役中,某支部队为了整个战局需要做出牺牲,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是否可以拒绝执行命令?他的理由就是:难道我的战士不是人吗?我们肯定很容易做出判断:军令如山!
这类案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有些容易选择,有些不容易选择。比如军人接受命令是天经地义,泄洪区也能接受,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已经固化了这些道理。但是,还有很多就难以决策,在管理学上赋予这类选择一个概念“多数人的暴政”。
“多数人暴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所以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说,什么是“暴政”?什么是自然权利?这本身就缺乏明确性,缺乏操作性。由谁来下这个判断呢?谁有权下这个判断呢?
在人类社会前行的路途上,我们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点所设计实行的规范,充其量是在这个时空点“最好的”。我们不可能在某个时空点设计实行了一套“完美的”规范,完美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现实到达的社会状态的下一站,从而使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对现实的不满、对完美的垂涎。
最后讲一个笑话。
英语考试,小明选择题全部选错了,老师说: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因为瞎蒙也能对四分之一啊。
所以,作为公共决策,搞砸一次很正常,搞砸多次就不正常了。如果全部搞砸了,一定要属于天赋异禀。比如当年的常凯申同学,好好一把牌,愣是搞成了相公。
当公共决策失灵了,多数人的暴政就变得很平常。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小人物K
小人物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