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每一个没有去过的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冰天雪地一毛不长的地方。我经常还会被问我的家到底在哪里,我只能用他们能感受到的语言来形容:“我家在宁古塔那嘎达”。虽然他们能些许理解那是个什么地方了,却更加深了那是一个苦寒之地的印象。但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四季分明,春天万物复苏、夏天凉爽痛快、秋天硕果累累、冬天银装素裹,到处都有农田与森林,到处都有生机。哪怕是冬天最冷的那几日,在茫茫的雪地里,松树也直愣愣懵懂地长着。
可有趣的是,我对松树最初的印象却是软乎乎的。种花要用肥沃的土,这时候,爸爸会带着我爬上山,找到一片松树林,从松树底下厚厚的一层松针下面挖一捧土。那层松针要有半米厚了,踩上去就像踩在云朵上,我总是走不稳跌坐在地上,却发现根本不疼反而好玩极了。这片松树林立刻变成了我的天然蹦床游乐场,走几步就要刻意跌倒,享受倒在厚厚松针云朵上的快乐。爸爸说这么厚的松针都是松树掉落的,就像是掉头发一样,要落好多年。
长大后,学习与工作占据了我的生活,我鲜少再有和爸爸爬山的时光与乐趣了。我还记得一次爬山的时候我妹妹还很小,我爸的腰也不好,不过也还是要拎着马扎牵着我妹去爬山的,足以见得他有多爱爬山了。后来他的腰差不多都好了,就总是要带着我去看离家有些距离的红松林,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终于看到了那一片直戳云霄的松林。我们走进这片森林,仿佛走进了时光博物馆,在这里,没有信号,声音仿佛凝结成了水滴,空气也安静下来。随手摸过一颗松树,看起来个头在这片里面没有很高也没有很粗,它身上的小牌子写着“500年”,在这里它还是个小朋友呢。几百年的红松到处都是,一千年两千年的也偶尔能遇到,每一棵都腰杆笔直目不斜视,就像是千年前集结的军队,散发着古老沉稳又安定的气息。我突然想到我爸曾经跟我说,他的陆军常服颜色是“松枝绿”,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妙了,军人就应该是这个颜色。
两千年前是西汉,这里的松树就已经开始生长。上千年的朝代变迁、社会动乱、动荡不安仿佛都不能阻止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每一棵树自成一个结界,兀自安静地沉稳地生长着,红松的树干长得慢,但是它不急,它总有时间慢慢长,吸收空气与阳光,和脚下的土地对话。它从不着急抽新芽,只等这一年树干长得足够结实了再去走下一年的路,等回过神来,它已经几十米高了。它从不低头只向天空,也许唐朝的达官显贵走过,也许清朝的落魄猎户走过,而今我走过,对它来说都是不重要的过客,重要的是自己的生长。它不说话,它也不需要说话,它在那里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下山,手机连上信号的那一刻,我仿佛从须弥山小世界穿越而归,手机还是那台手机,可我不再是那个我了。
 小人物K
小人物K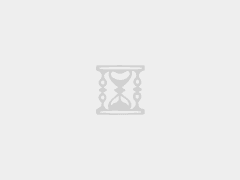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
低调:真球王的内涵